
不知不觉上科大也要十周年了,突然想翻翻之前的邮件,找回一些校园生活的片段,却是翻到了大一时候选的现代文学写作的课程习作,觉得很有意思,应当保存下来,就记在了这里。这篇作业的主题大概是以另一个主人公子君的角度复写鲁迅的《伤逝》。
我想我不知道以怎样的情绪和姿态回望过去一年的生活,那些快乐的笑语似是总能在我苦涩无措时清晰地浮现,是一种极富有生气的活力。对于寒冷冬夜中的麻木身体而言,那些最开始的活力大概就是对我这个已是失去的人的唯一宽慰了。
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涓生的会馆里的那间屋子,那张桌子,那张椅子,那张床,窗子外面的那棵槐树,暮春时候的带点湿气却已经并不刺骨的风。我坐在床边,他就忽地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以一种孩子般的天真而又害羞的表情,一点一点的将右膝弯下落在地面上,那时的他的目光是热切又飘忽的,他伸出手来,握向了我的激动着颤抖着的手,含着泪看向我。我记得那时脸上能够明显的感觉出非常时的温度,颤抖着激动着,我没有说话,我们这样无声地飘忽地热切地看着彼此。我很怀恋,即使是后来的那样决绝的离开,也依旧怀恋。
至于经常将这段昏黄的油灯下的记忆拿出来,将那几句熟捻的不能更熟捻的话反复读诵,我喜欢看跟涓生提起时他的落荒而逃似的有趣表情,我猜那时的我的脸上是满是天真的,我是那样的纯粹的喜欢着那段片刻的记忆,到了后来的刺骨冬季里,在我独自在吉兆胡同的时间中,这也是我为数不多的除开那些琐碎家事后的一点点慰藉。
那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便以一种十分频繁的频率到涓生的那间屋子去。我们似是漫无边际的随意谈着天,我便能轻易地忘却之前几个钟点里的与父亲和胞叔的那些吵闹争执。我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他的声音是那样温和,坚定的语气中带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意味,我则像是一个乖巧的学生一样,更多时候以一种崇拜的目光望向他,望向他……
“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那一天我便是这样地对着胞叔和父亲说,他们当时的神情我甚至都无需回忆,因为现在他们无时无刻不用这样的神情看着我,恼怒,叹息,兴许比起现在少了些怜悯而多了点嘲讽。若是在与涓生相处这些时日之前,我大概也是没有这般的勇气的,那时的力量似乎都是来自涓生,而当我所憧憬的一切又被这力量无情夺走时,便是真真正正的灰色和绝望。
我把这些话跟涓生讲后,他大概惊异于我作为女性的这种勇力,目光中多了一点尊敬的意思,我是很欣喜的。从此后的半月时间里,我俩大部分时间都是同去寻些住所,我讨厌那些房东们的看向我们的怪异神情,似是我们之间有着见不得阳光的苟且龌龊,但我是丝毫不畏惧这种目光的,甚至对它报以蔑视,对于往后生活的向往便是那时我最大的力量,我以为在此种力量下我不拒拍任何人任何事,但却是从未想到过最后竟是生活本身给了我最痛彻的击打。
我再也没有了那种对抗一切的勇气,甚至现在已经无法独自站起身来,连自身的这一点点阻力都已足够击败我。我想看看窗外的那几棵树,像是原先初识涓生时那样,可它们却也早没有了甚至枯黄的叶子,如我一般,只能是苟延残喘着地过活……
我和涓生最后是找到了一个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屋主住正屋和厢房。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家是极欢喜的,终归是有了自己的处所,置办了些家具,便更像是一个小家了。我让涓生去买了几只小鸡与房东的鸡同养,又去买了只狗,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阿随,是想能够时时跟着我俩。
生活便是这样,涓生白天照旧去局里工作,我则是每天在家中饲鸡饲狗,准备一天的三顿餐食。我本来是不怎么会做饭的,幸的是每天也就这些事情,花的功夫多了自然也是不会有太差的结果,我希望给予涓生一种真正的家的感受,不再是原先的随便的,漫无目的的生活。于是我便独自在家中,与鸡和狗待在一起,上午去附近的菜场买些菜,然后就是午饭,下午再稍微愣一会儿便又是到了晚饭的时候。于是当我闲在家中,便只好回忆些以前与涓生一起时的那些谈话,多了之后,也就无比熟捻,至于有点疲倦了。
其实想来事实上我是不喜欢这种生活的,但是爱情似是有种盲目的不顾一切的力量,使得我可以忽视掉那些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乏,天真地以为会有幸福的顺利的生活。我不恨涓生,也许我就如同他一样,也是厌烦了这样的日子,只是他是那个先说出来的人,于是我就变成了似是弱势应该难过的那一方。但我想,大概我俩的心情是相似的,是没有那么多高下之分的。
此时的我的心绪是复杂的,桌上的那一盏油灯不断摇晃着火焰,晃得我心烦意乱,我无意对抗肉体上的病痛,我想这是无意义的,当精神绝望之后,生活绝望之后,肉体的病痛与之相比就也慢慢地变得无关痛痒一般。可我总还是想起原先的那些画面,即使我知道我们的决裂是怎样也不能避免的。我慢慢意识到,爱情是一种冲动,冲动中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实际上的那样困难,可是当时间开始缓缓用力,冲动被渐渐挤散,就只剩下了生活的琐碎和物质的压力,而我们,是没有共担这种压力的契合的。
独自在家的哪些日子里,我常是压抑着自己的烦躁装出笑容面对着涓生,起初还并没有什么,直至涓生收到了一封辞退的电报,我在那时才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即将面对的艰辛的生活。
他说他会问问《自由之友》的编辑可否译些文章或是发表些小品,还打算在报上登广告看看有没有些钞写或教读的事情可以做。其实我是明白了我们已无法继续伪装下去,但却也无法接受。此后涓生便在家中写些东西,我是没有兴趣的,依旧只是每天做饭。我原先以为白天的燥意是因为缺少陪伴,然而等他真正时刻待在家中,我心中的烦闷却是一点都没有减少,甚至会因为白天仅有的催他吃饭的这点交谈而更加烦躁。
天气渐渐凉了下来,我们却依然是盼望着生计来源,家里早已是没有了煤块,隔着不大的窗户也能够感受都极其清晰的寒意。涓生白天不知道去了哪里继续写东西,而我便只能够留在家中忍着这种苦寒。那几只鸡早已是被我们宰掉了,至于连饲鸡这点事情都不再有。我常常是坐在床上,甚至不再做饭,只是这样呆呆地看着面前的虚无,一天又一天地终日恍惚着。
然后便到了那一天,我想我对于那天的记忆是极深刻的,但我不想回忆,就算仅是想起我的这副即将破碎的身体也会感受到那天夜里的深深的寒意。
我应该早就预料到了,但当真正来临时,感受还是那么失意凄凉。我收拾好了自己的不多的几件衣服,最后又仔细地打扫了一遍这两间住了大半年的屋子,便是关上门走了。我没有给他留信,也没有让房东给他留话,就这么径直走出了这个胡同,坐上了父亲叫来的车子,就这样沉默地走了。
一路上父亲似乎跟我说了些什么,然而我是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责备又怜悯的眼神。
我不知道涓生后来如何,是否还住在吉兆胡同里,是否找到了生计。至于我,回来后便几乎没出过门,一方面没了兴致,一方面身体是愈发虚弱。我不想再想起过去一年的种种,但却又总是习惯性的在无所事事时在脑中进行回忆。我想我是不会再见到他了,事实上,我也不再想见到他了,这不是因为我对他存有任何的怨恨,仅仅只是因为我再也不想,面对那些琐碎和生计了。
偶尔我还能见到胞叔,他便总是一副轻蔑的面孔对着我,像极了趾高气昂的胜利者,我再也没有力气与他争吵了,我能做的,只剩下吃力地从床上坐起身来,转头望向窗外连枯黄叶子都已掉落得干干净净的那棵树。
我把这一切写下来,为了纪念这一年的曾经快乐过最后厌倦了的光景,为了真真正正地能够忘却这一切。对于涓生,我不再怀有对他的任何爱或恨,这将与我再无任何干系。
我要遗忘,遗忘给过往送葬的日子。将欢喜与爱恨深埋在不知名的土壤里,唱一曲挽歌,然后不再挽留,我要跳入孟婆身后的三途河里,洗去身上的怨念和不舍,对岸,那才应该是我的新生。
就让这一切都逝去好了,我不会再伤感,记住的只留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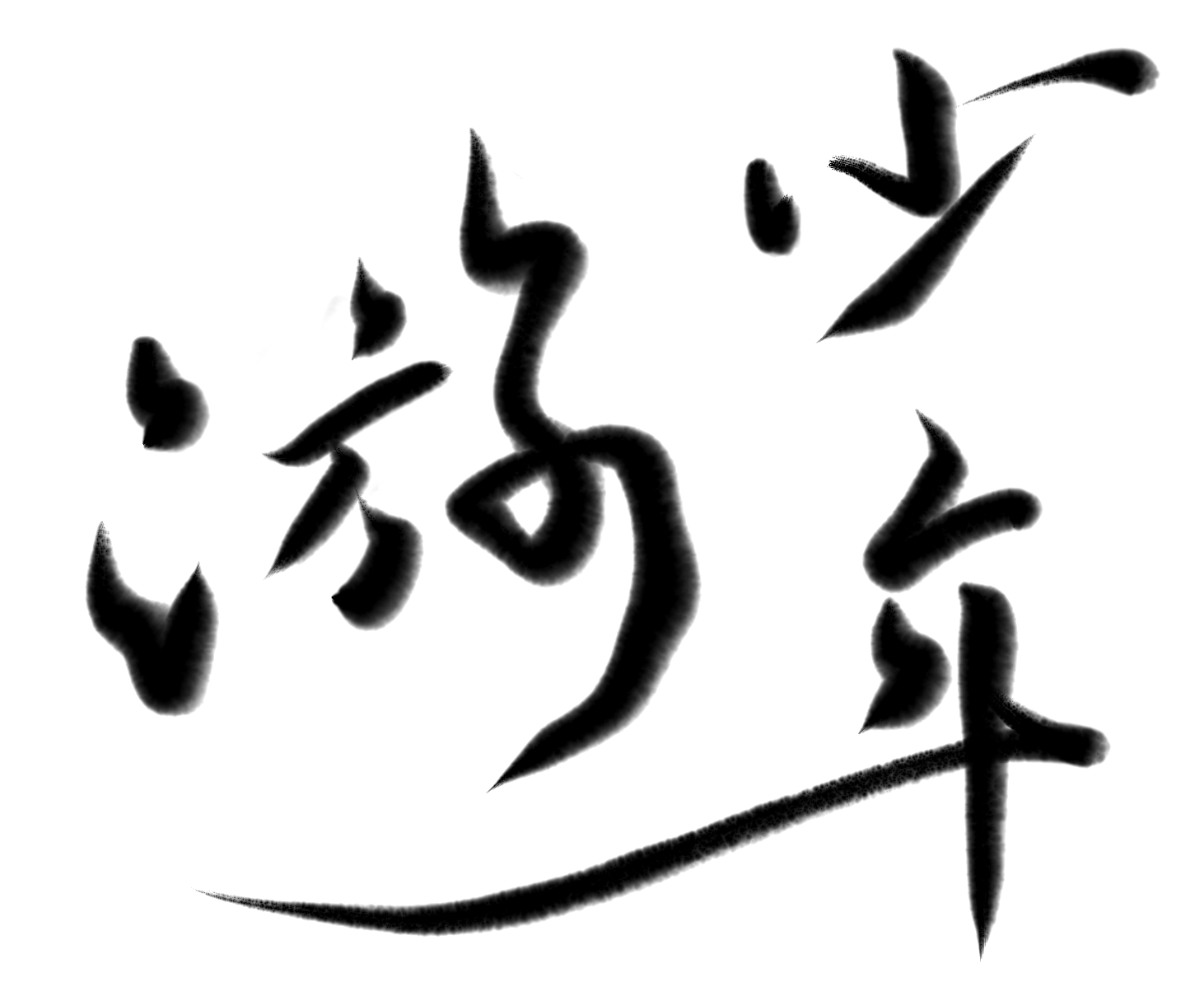


Comments